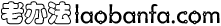戏剧名言
16.书信体非常方便,既可以自如地叙述事件和人物,也可以回顾过去,同时也可以去展示亲身经历。在人物的转换上比第一人称还自由,还宽泛。小说后面的话剧与前面有联系,有呼应。"我"与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通信,讲述"姑姑"的故事,并商讨如何将"姑姑"的故事写成话剧。最后由小说文本跳到戏剧文本。舞台上出现了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青蛙,是超现实的情节,当然话剧里也有对当今生育现状的展示和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抨击和讽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17.我国的悲剧不能给人由崇高而引起的激情,相反的,使人心中萦绕着个人灾祸的折磨,心情动荡以至自我蒙蔽,尤在结局时,常常让替代性祸灾使人们软弱,带着内心的苦闷,希冀一些安慰和对善行。正义的勉励,更大大地削弱了悲剧的力量。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形成的等级与正统观念,被提倡的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要绝对地战胜与此相左的其他观念。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实际上只是诗的正义,而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我国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钱钟书
18.第一,我们是从农耕文明来的,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实际上是在村落里,而不是在城市中;第二,我们的村落不只是数量多,还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板块,每个村落都有它独特的风土民情,有一种说法,叫做“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村落里面;第三,村落里面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学、手艺,等等。就拿民间文学来说,我们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最近十年整理的民间文学,光整理好的就有九万字。我觉得我们村落的文化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深不见底,浩无际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
羊城晚报:您说过“古村落的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古村落为什么这么重要?
作家,画家 冯骥才19.我这个撤退实际上也是一种作家的用语,实际是向民间文化里面搜取创作资源,从个人经验里面寻找创作灵感,这是我从1987年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一个追求,到了《檀香刑》,所谓的“大踏步”,直接汲取民间的这种通俗戏曲的样式放入小说中。《檀香刑》是一个典型的把小说和戏剧嫁接的文本,里头有很多寓意和民间戏曲,例如传统的“茂腔”,我如果直接这样称呼会影响了我的构思,为了避嫌,改成“猫腔”的话我就可以随意写了。“撤退”是军事术语,文学创作上用它来描述其实很不准确,就像时尚一样,什么叫时尚?什么叫前卫?什么叫后卫?50年前的服装,中山服,现在我们穿了,也很先锋,如果我们现在有人穿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装、长袍,又变得很前卫很后现代了,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无所谓古和洋,无所谓先锋和后卫。现实主义的写法,前面的高山已经不可逾越了,对我们来讲,在小说的形式上追求点新意。《生死疲劳》形式上有一点章回体,写作时会很方便,这一章要写什么,读者阅读也很方便。我看到批评家讽刺我,雕虫小技。
人物周刊:您说,《檀香刑》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生死疲劳》也是某种撤退,这种“撤退”与“回归”会一直进行下去吗?您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